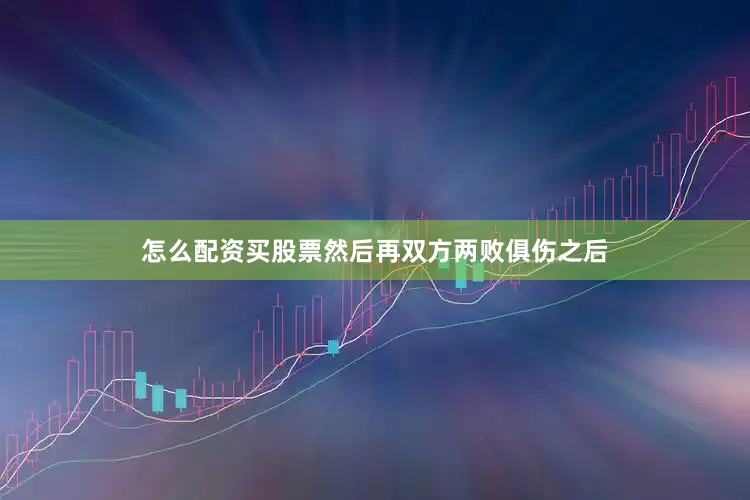老屋院角的梧桐树下,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皮烤红薯炉总在秋冬时节冒起暖烟。圆柱形的炉身裹着一层厚厚的黑炭灰,是常年烘烤留下的印记,炉口用铁皮片卷成弧形,边缘被爷爷的手掌摩挲得发亮,炉底的通风口还挂着半截铁丝,是当年爷爷亲手焊上去的拉手 —— 这只烤红薯炉跟着爷爷走过二十多年,它烤过霜降后的蜜薯、雪天里的白薯、开春前的紫薯,暖过放学归家的我、串门的街坊、赶路人的手,把院子的烟火、爷爷的疼爱、时光的香甜,都悄悄封在焦脆的薯皮与滚烫的薯肉里。
第一次蹲在炉边等红薯,是个初冬的傍晚。西北风卷着梧桐叶落在院角,爷爷蹲在炉前,正用铁钩勾开炉口的盖板,里面的红薯泛着焦红,热气裹着甜香 “呼” 地涌出来,呛得我直揉鼻子。“再等会儿,最里面那几个才烤透。” 爷爷笑着把我拉到身边,用粗糙的手掌捂住我的小手,炉壁的温度透过铁皮传过来,连带着爷爷掌心的暖意,把寒意都驱散了。那天我捧着爷爷递来的烤红薯,指尖烫得直换手,却舍不得放下 —— 咬开焦脆的薯皮,金黄的薯肉冒着热气,甜丝丝的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,连指尖沾到的薯泥,都要舔得干干净净。暮色里,烤红薯炉的烟缓缓飘向天空,与远处的炊烟缠在一起,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画面。
爷爷的烤红薯炉里,藏着无数个关于冬天的印记。炉口内侧的铁皮上,有几道深深的划痕,是我小时候用铁钉刻下的 —— 那时候总嫌红薯烤得慢,就用铁钉在炉壁上画画,爷爷看到了也不生气,只是笑着说 “别划着手,等会儿红薯就好”。现在每次看到那些歪歪扭扭的划痕,都能想起爷爷蹲在炉边,一边添炭一边陪我说话的模样;炉底的炭灰里,总埋着几颗没烤透的小红薯,是爷爷特意留的 “念想”—— 街坊家的小阿妹怕烫,爷爷就把小红薯埋在炭灰里温着,等她放学来,刚好能捧着暖手又不烫嘴。有年雪天,小阿妹踩着雪来拿红薯,爷爷从炭灰里扒出红薯,用围裙擦了又擦,才递到她手里,“慢点儿走,别摔着”;最特别的是炉边的那只粗瓷碗,里面总盛着清水,爷爷说 “烤红薯燥,吃完喝点水润润喉”。我小时候总爱用那只碗接炉口的热气,看着水珠在碗壁上凝结,再把水倒进炉里,听着 “滋啦” 一声响,爷爷就会笑着刮刮我的鼻子,“小调皮,又浪费水”。
展开剩余48%烤红薯炉最 “热闹” 的时候,是腊月的集日。爷爷会推着炉子去村口的集市,炉口用棉被裹着保温,远远就能看到暖烟飘在人群上空。赶集的人路过,总会停下来买一块:挑担的货郎放下担子,捧着红薯边吃边跟爷爷闲聊;放学的孩子拽着妈妈的衣角,非要买一块才肯走;连路过的牧羊人,都会牵着羊过来,买块红薯揣在怀里暖手。有年腊月,集市上飘着小雪,爷爷的炉边围满了人,我帮着递红薯、收钱,手冻得通红,心里却热乎乎的。那天收摊时,爷爷从炉里掏出最后一块红薯,掰成两半,一半递给我,一半自己吃,雪落在我们的肩头,红薯的甜香却把寒冷都融开了。
后来我去城里读书,每年冬天,爷爷都会烤好红薯,用保温桶装好,托人捎到学校。桶里的红薯还冒着热气,剥开薯皮,里面的糖心泛着琥珀色,咬一口,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有次视频通话,爷爷说 “今年的红薯甜,等你回来,我再给你烤”,镜头里,他蹲在炉边添炭,烤红薯炉的烟依旧缓缓飘着,像在诉说着牵挂。
去年冬天回老屋,爷爷的烤红薯炉还在院角。他的背更驼了,却依旧能熟练地勾开炉盖,只是添炭时,需要扶着炉壁慢慢起身。我蹲在炉边,帮爷爷递炭,暖烟裹着甜香,又一次漫过院角。“尝尝,今年的蜜薯特别甜。” 爷爷递来一块红薯,我捧着滚烫的红薯,看着爷爷满是皱纹的脸,忽然觉得,这只烤红薯炉烤的不是红薯,是岁月的甜,是爷爷的爱。
暮色漫过院子时,烤红薯炉的烟渐渐淡了,梧桐叶落在炉边,爷爷正用铁钩把炉口盖好。我知道,明年冬天,这只烤红薯炉还会在院角冒起暖烟,还会烤出甜丝丝的红薯,暖着归人的手,也暖着岁月里的牵挂。原来有些温暖,真的能像烤红薯炉的烟一样,跨越时光,永远留在心里。
发布于:湖北省广盛网-线上股票配资-配资开户-股票如何开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外盘配资公司委内瑞拉正在举国构建立体化防御体系
- 下一篇:没有了